李汉松评《旧世界的相遇》|万变不离其“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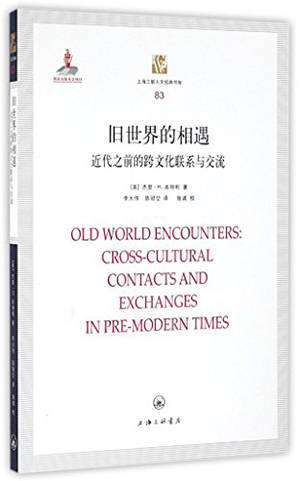
《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美】杰里·H.本特利著,李大伟、陈冠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2月出版,187页,38.00元
欧美的左翼世界史家在讲授通识课时,大多履行一套政治礼仪:忏悔十九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社科前辈们如何以基督教为模本,为高加索、南亚、东亚乃至玛雅、非洲和马来波利尼西亚的文化冠上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教义”:穆罕默德ism、孔夫子isme、佛陀ismus……而那些受封“科学”身份范畴的当地民众往往不知所云。在战后去殖民浪潮的浇灌下,西方史界这一抹良知逐渐生根发芽,智识赎罪的自我批判工程纷至沓来,言必谈“去西”“去殖”之势从边缘突入中心,“比较史”“交流史”从潮流升为主流。
然而,最易“去”的往往是史料、语言、地理分布的偏畸,而非概念框架和问题意识上的桎梏。前现代文明的邂逅与演进,史料凿凿,但如何重新排列组合、建构叙述,则透出史家个人语境的底色。杰里·H.本特利的《旧世界的相遇》以“改宗”为“主导动机”谱写了一曲“西式去西”宏篇交响乐。循着曲子的节奏,本先生以盘根错节之才、八面玲珑之笔,援引宗教与世俗、涵化与同化、迫害与抵抗等阐释工具,追溯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之前的“长时段”“长距离”交流,戴着西方宗教史的镣铐跳了一段全球文化史的热舞。
万变不离其“宗”
本特利先生开篇承诺,他要弥纶统摄古代文化群体相遇时的冲突与交流、扬弃与融合、坚持信念与相互改变(原著第5页、译著第3页)。然而综览全书,千万般际遇如顄淡滂流,统统汇入宗教关系这一潭池泽。诚然,本先生秉笔荷担,也谈科技、贸易和瘟疫,但这些无非是基础活动,托举着宗教际遇的上层建筑——商人网络引入了异域宗教;科技促进了宗教的扩张;瘟疫摧毁了当地宗教……本先生也斟酌“制度”,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推动大规模改宗的社会经济机制:宗教群体之间的差异化税收、宗教团体之间的金融资源转移、任用政治军事长官时的宗教信仰偏好、限制宗教服务与仪典的限制与激励、关闭乃至毁灭教堂、神墓和庙宇……(原著第12页、译著第8页)。本先生不断讨论“语言”“习俗”和“价值”,但落到实处的却总是宗教信仰。有时,他似也不好意思再敲打“宗教”,便改称“信仰和价值”“文化扩散”“异国文化传统”,但即便是明言“政治、社会和经济激励”,激励的也是“大规模改宗”。
本先生具体提出了如下三种改宗模式:文化相遇时,(一)能自愿改宗、高层赞助、民间同化便罢;(二)不愿改宗便抵抗;(三)无法抵抗便开溜,如摩尼教流亡泉州、帕西人遁入印度——行笔至此,不妨顺带一提:北京丽都饭店的“泰姬楼”老板Pastakia先生便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帕西人,精通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的语言学著述,笔者与他谈过吠陀和阿维斯陀语的比较研究问题。倘若溜之大吉也无法可想,便只好接受“熊熊烈火焚我残躯”的命运。
第一种和平改宗可以进一步细化区分:不但有西哥特人在罗马世界内部的同化与皈依(原著第13页、译著第9页),也有佛教徒、景教徒和摩尼教徒游走欧亚大陆时,在几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下自然促成的“自由结社式改宗”(Conversion by free association)。这一颇显乌托邦色彩的概念尤其值得社会、宗教与政治理论学者注意。姑且不谈这一表述的渊源及其与《美国权利法案》的古怪共鸣,历史学家有必要追问:是否存在过集体的“自由结社式改宗”?个人改宗与集体改宗之间、菁英改宗与大众改宗之间、宗教改宗与世俗改宗之间,究竟牵动着什么因缘?出身欧洲宗教文化史的本特利先生有言在先,他无法证明菁英的皈依如何导致群众的改宗:也许是强迫,亦或是渗透,更可能是国家背起旧宗、赞助新宗,提供了结构性激励,营造了改宗生态。但不论如何,他认为“自愿改宗”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范畴,因此立誓要采用这一视角来书写文明交流(原著11页、译著删去)。想必“自由结社改宗”是“有用”的,不然本先生也写不出这部鸿篇巨帙。但语境化批判“自愿改宗”这一概念也同样“有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限制“自愿改宗”阐释社会行为的效力,而不至于混淆“自由”与“结社”的古今意涵。本先生说得不错,我们无法获取菁英改宗时的“心理状态和个人动机”(原著11页、译著第8页)。我们也只能暗暗猜度,却无从获知本先生的宗教意识底色缘何而起。不过本先生批评强制性改宗,强调“自由结社式改宗”,颇显开明,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着现代西方社会经历过宗教战争与宗教改革、世界大战与帝国殖民后做出的权利承诺。
但不论答案如何,我们都不难发现:本特利感兴趣的文明交流只是宗教传播史:佛教和印度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摩尼教和聂斯脱里派在印欧的传播、伊斯兰教在沙哈拉南北与河中地区的传播……我们不禁疑惑:宗教传播是“文化相遇”的子集还是别称?倘若是子集,宗教传播这一机制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具有多大阐释效力?如果文化相遇即宗教传播,那么此书的副标题何不改为《近代以前的跨宗教联系与交流》?本先生解释了:他所说的“改宗”不是个人的精神和心理,而是“近代之前人民接受或适应异域文化传统的过程”(原著第8页、译著第5页)。但纵观全书,本先生感兴趣的固然不是个人皈依外来宗教,但确乎是集体皈依境外宗教。他所说的“社会改宗”无非是“全社会的宗教改宗”,而不是更宽泛的社会演变。
事实上,本特利也有意屈伸“改宗”这一范畴,指一种在多群体互动压力下的相互改变的现象。可惜他实际操作起来,便像是被人工智能事先编好了程序一样,不论如何“凌云健笔意纵横”,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不只是我读罢此书的印象,也是国外学者,甚至是本特利的美国同行批评此著之关节所在。世界史名宿威廉·麦克尼尔之子,环境史家约翰·R. 麦克尼尔在《世界史学刊》的一篇书评中便直言不讳:“本特利没有明言他谈的‘文化’究竟何指……他所说的文化,其实意指宗教。他追溯文明之间的邂逅,但是文明(主要)是依据宗教而定义的,而他笔下的文化传递、改宗和融合,也几乎全部是宗教意义上的。”(见J. R. McNeill,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Jerry H. Bentle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1) 1995: 130-132, at 130)麦克尼尔不确定本特利说到中国时,谈的是儒家还是儒教,当然本先生也从未解释过这二者的差异。
古代社会的互通有无当然绝不止于狭义的宗教改宗。如信德、旁遮普、俾路支史诗,无不大谈宗教群体之纠葛,但也充满了爱恋与仇恨、世俗与超然、政治与外交这些实质性的关系规范。甚至可以说,即便“改宗”问题也不止于“改宗教”而已:保加利亚人改宗东正教,涉及了族权与皇权的认知、民族与帝国的意识、语言和文化的竞争、贸易与关税的争论。斯拉夫民族的改宗是个经典的文化相遇案例,可惜本先生并不怎么谈斯拉夫,也不大讲查士丁尼之后的东罗马,只是说到塞尔柱、奄蔡时才不得不提,忽视了拜占庭在“旧世界相遇”中的巨大作用。倘若本先生真正着迷于“改宗”,那么拜占庭“改宗”基辅罗斯这桩大事,总该入得了他的法眼罢?本先生为何绝口不提?全书只出现了四次“罗刹”,均是蒙古西征时候的事了。俄罗斯毫无铺垫,昙花一现。本先生这位泰西硕儒愿意大篇幅探讨中国史,却忽略东欧和斯拉夫,这一现象耐人寻味。
丝路上的改宗
本先生遥想丝路时代,多元种族和文化相互交融,甚至共享“伦理和道德标准”,但旋即便宣布:这些伦理道德就是“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价值观”(原著65页、译著54页)。如此标签化处理中、西、印传统,也体现于作者的史料选取、地域侧重和历史分期。
本特利谈印度,自佛教始,空口敷衍“印度教”,几乎不谈佛教之前和之外的南亚传统。如此佛教中心论的南亚史观,写出的“旧世界相遇”既不“旧”也不“世界”。为了直击丝绸之路,本先生略过吠陀时代横跨印伊大陆的长距离交流,笔锋直指改宗佛教的阿育王(原著44-46、92页,译著35-37、78页,本特利关于阿育王的知识主要来自Romila Thapar, Asok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aury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和B. G. Gokhale, Asoka Maurya, New York: Twayne, 1966这两部书),应付南亚了事。至于印伊走廊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本先生仅提了一句:曾有佛教徒去了安息帝国的东端,但很可惜,这些人没有为伊朗地区带来任何“社会改宗”(原著46页、译著37页,译文作“波斯帝国东部”,应为安息或帕蒂亚帝国东部)。作者如此三令五申,读者再愚钝,也慢慢体味出了:不涉及阿育王级别的大规模宗教改宗,是唤不起本特利先生的兴趣的。
本先生少谈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化,而是专注于基督教化后的西罗马世界。当然,早期基督教不乏替代品和挑战者,譬如密特拉崇拜(原著59-60页、译著49页)。本先生含糊地说罗马的密特拉与波斯的密特拉不大一样,却不解释二者之关联与异同,尤其是罗马军人长途迁徙触发的文化创新,因此错失了一段“旧世界的相遇”。他也没有借机谈谈波斯密特拉Miθra与吠陀密多罗मित्र之关联,再度错失了一段“旧世界的相遇”。其实,印欧文明的密特拉传统直接涉及族群之间的友谊与契约,值得古代文化交流史家大书特书。
中国这方面,本先生晓得“汉武灵王胡服骑射”,但此外闭口不谈任何西汉以前的跨境交流与民族融合。在这位“改宗史”家看来,汉匈关系竟是“儒教/家与匈奴”的关系(原著35页、译著24页)。他似乎迷上了中行说(原著38-41页、译著27-30页),不惜笔墨反复寻思:中行说究竟是改宗了匈奴,还是警告匈奴不要改宗?中行说又有没有改宗?本先生语境化分析了太史公的“作者意图”,但话锋一转,又回到了主旨:什么中行说,什么金日磾,这些具体案例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改宗”。
思想史家晓得,“伦理和道德标准”不是率由旧章,而是流动争鸣;不是从石碑上拓下来便可以相互比较的经书铭文,而是在审议和辩论中不断再想象的语言和规范。本先生治文化史,静态处理“文化价值观”,浑然不知中、西、印等传统苦苦思索过社群之间的规范性关系,留下过发人省思也不无争议的智识遗产。这些思考是阐释资源,而非教义教旨。与其在古史的迷雾中捉摸“宗教”的幻影,流水账似的记录一切似是而非的“改宗”,不如深入文本语境,探究社群相遇时如何言行——不论他们改宗还是不改宗。
扩张下的改宗
本先生爬梳文化史时“万变不离其‘宗’”,反倒是在宗教史的荫蔽下,才彰显出文化史的气质。《传教士、朝圣者与世界宗教的扩张》一章挑明了宗教的中心地位,却阐明了倭马亚和阿拔斯、法蒂玛和穆瓦希德治下的种种社会境况:税收、教育和民族关系。本先生延续了西方世界史的传统,重视伊斯兰世界。但比起老一代接触近东学的世界史前辈和新一代受过伊斯兰研究训练的国际史学者,他对早期伊斯兰史料的把握仍有欠缺。举一个细枝末节来说明,他引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手文献断言:早期伊斯兰扩张依赖骆驼(原著90页,另见Richard W. Bulliet, The Camel and the Whe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87-110),又重复了一段历史迷思。若说近东、中东和北非的骆驼至少从公元前900年便开始搬运物资,这无法解释公元700年穆斯林征服的“回归不连续性”;若说骆驼可以上战场,则须小心立论。战马怕骆驼,但比驼队擅长出入枪林弹雨。早期的骆驼骑兵大多是弓弩手和运输队。步兵骑着骆驼迂回包抄,增加移动力,但真到肉搏战的时候,常常选择下驼归队。因此,原始史料很少记载撒拉森骆驼骑兵的正面激战。
除骆驼外,本先生另有他法解释早期伊斯兰“突然”而“爆炸式”的扩张:拜占庭和萨珊王朝的“腐朽”(译文作“衰落”)和阿拉伯人的“强烈热情”(译文作“强烈的战争热情”,不确,原文指作战时有着强烈的来自宗教信仰的热情)。这种叙述陷入了刻板印象,忽略了阿拉伯-拜占庭关系史的复杂性。阿拉伯与拜占庭最早的直接冲突,要追溯到一代英主希拉克略统治的晚期,说战事连年、国库空虚是真,但谈不上“腐朽”,甚至不是“衰落”而是“中兴”。时间快进到马其顿王朝:拜占庭大反攻,收复亚美尼亚、北叙利亚、东南欧和南意大利时,难道是轮到东正教人迸发出“强烈的热情”了么?“成情拜朽”——如此读史,未免懒惰。
《宗教》这一章不全是宗教,但稍稍偏离,便自行绕回。譬如,本先生说唐朝受中亚影响,体现于歌伎的音乐、女人的胭脂、贵族的语言,看似脱离了狭义之“宗”。但很快,他便回过头来说唐朝没有怎么影响中亚,因为“儒教”“道教”没有扎根印欧草原(原著88-89页、译著75-76页)。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文化传统即宗教传统”,也不宜搞双标:唐人听胡乐便被“影响”了,但突厥人必须炼丹、捉鬼、拜太上老君才算被“影响”,恐怕不严谨、不连贯,也不公平。

《契丹还猎图》
游牧者的改宗
本特利谈中古欧亚大地上的游牧者,也仰赖宗教史的视角:菁英群体内部的改宗与不改宗。这一现象贯穿第四章,厥繇庞杂,实难一一厘清拾取,在此仅以本特利先生的契丹学见解为例予以说明。
本特利依据魏复古与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等二手文献试图论证契丹人不怎么信儒教,这结论不一定荒谬,但他的叙述却深陷阐释学困境。譬如,本特利称萧陶苏斡女、耶律奴妻萧意辛为“契丹公主”,说她很是懂得孔夫子,发表了“修己以洁,奉长以敬,事夫以柔,抚下以宽,毋使君子见其轻易,此之为礼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厌魅获宠,独步愧于心乎!”这般高论。后宫女子闻之,“深感尴尬”(deeply mortified)——本书中译者特地引入了《辽史·卷一百七·列传第三十七》原文“闻者大惭”。本特利因此得出结论:可见“在契丹统治阶层内部,中国价值观仅仅吸引了少数人,即便是在菁英社会中也没有赢得广泛的拥护”——这便齐齐整整地形成了中国儒教和契丹信仰的对立。倒也奇了!倘若广大契丹女性不认同礼法,为什么在听到萧女士狂飙礼法说教后要“大惭”呢?难道不应当像元昊番汉对立地慷慨陈词“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吗?任何受过语言哲学和思想史训练的学者都明白,“羞惭”的基础是伦理认同。此书“中译本序言”提到本特利先生“较之思想史……更喜欢文化史”,但这里我们不禁感慨:即便是依赖二手翻译文献的mortified(羞惭、尴尬)一词,中规中矩的历史学家也得不出“大多数契丹女子不待见礼法”的反直觉结论来。当然,我们可以再深究《辽史》这段叙述的文本与语境:是谁在书写契丹女人?“美姿容”的意辛是否如此言说,又为何如此行为?娣姒何以厌魅?倘若这是一群北宋女人,是不是人人讲得出“中国价值观”?而那些讲不出礼法的听到头头是道的纲常高论,是否也会“大惭”?在那种情形下,又是什么本土信仰与外来信仰之间的张力在作祟呢?
本特利先生的契丹学新发现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契丹人与汉人之间的交流纯属“偶然”(haphazard),理由是即便过了两百年,汉人仍然“gagged at”马奶酒。据我所知,中古和近代早期英吉利动词gag(gen)是在十九世纪才从“堵嘴”“噎喉”发展出“打诨”这一层意思的。巧得很,我读到此页时,正如契诃夫、斯克里亚宾一样在饮马奶子酒解忧,一时间竟也堵住了嘴,噎住了喉,不禁同样gagged at了本特利先生:既然立了汉人不爱喝马奶酒的高论,怎也不注明文献出处?
《旧世界的相遇》谈非西方文化时跌入此类阐释学泥潭,倘若是数据不足不确,则有情可原。麦克尼尔曾为汤因比辩护:世界史家必须吸收大量的信息,在脑海中发酵加工,才能输出庞大的叙述,过程免不了摩擦和成本,产品难免失之精准。要求本特利先生研修契丹大字小字,兼通回鹘、女真、西夏诸文再出版大作,不无苛刻之嫌。但是这些疑难果真是知识量不足所致么?实际上,本先生无需“皈依”内亚语文学,只需跳出自囿的概念牢笼即可规避智识误区。倘若他不生搬硬套贯穿中古和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文化史的皈依与同化问题,而是打开心智,仿效“年鉴”先贤捕捉时代心态,亦或仿效微观史家“察秋毫之末”,探寻跃然纸上、字里行间、超越宗教性的社群关系,便不至于陷入四处寻找“皈依与不皈依”的旋涡了。倘若查证史料之前已有了叙述框架,而框架又预订了结论,那么这种佐证便沦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了。倘若在探索旧世界如何相遇之前就钦定了“相遇即是选择皈依或不皈依、同化或不同化”,那么我们只是在更广阔的海疆中不断复制欧洲乡镇的改宗史罢了。
从契丹问题可见,本先生有一套既定的思维模式: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摇摆于改宗与不改宗之间。为了在改宗光谱上画一个点,他必须先脸谱化地概括两种文化,再研判二者之间“改宗与被改宗”的关系态势。譬如,他必须简化契丹文化为萨满文明、宋文化为儒教文明,再读二手文献,得出结论:“契丹没有怎么被改宗。”与此同时,他忽略了文明的多维度影响,譬如,契丹对唐与五代文化的继承也与宋形成了反差。其实,“唐文化”中也包含丝路东段的文化交融。宋人丝路尽失,与盛唐的西域文化严重断层,因此反而能在辽土感知“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唐韵。话说回来,是否存在过一种同质而恒定的“契丹文化”和“中华价值”,撑得起这张“改宗与被改宗”的光谱?也许,本先生的模式化思维能为爱好历史的当代社会科学学者提供借鉴:建造一个描述性结构模型,“捕捉”一个“核心张力”启发来者,不失为一桩美事。但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要在描述的简易性和叙述的细腻性之间做出权衡。
发现中的改宗
第五章《面向新的世界秩序》是“旧世界相遇”与“新世界相遇”的交界面。作者试图停留在“旧世界”,刻意规避进入近代早期以欧洲为主线的大航海时代,但仍然以航海与发现、扩张与改宗等欧洲殖民史主题为线索编络史料、敲凿史论。
在本先生看来,十四世纪晚期到十六世纪早期这段世界史可以归纳为:中国人半途废止的海路多宗教交流、伊斯兰的成功东扩、西南欧颇可诟病的基督教复兴。大约是因为不够“跨宗教”,这段时间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际关系、南亚世界的文化际遇、非洲的跨区域交流史,统统被忽略了。即便世界史是国别史的“聚合”,这一章也略显力不从心。
全书曲终落幕时,本先生哀叹殖民扩展以来的“去文化”现象:无数可供替代的文化道路“迫于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改宗”,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则坚持丝绸之路式的文化相遇:通过商贸网络的拓展触发“自由结社式改宗”。作为美国人,本先生尤其惋惜南北美、加勒比和太平洋群岛的大批量“去文化”。他想知道:日后是否仍有条件复兴这些泯灭的文化资源?这里,本先生对文化解读,甚至是“改宗”一词的容量不无升华。譬如,他提到欧洲定居殖民者加那利群岛的古安切人、加勒比的阿拉瓦克人和泰诺人、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带来疾疫,导致原住民的“政治和文化权威人士”也大规模死去,影响了社会资源的传承(原著183-184、译著161页)。当然,本先生仍在讨论宗教习俗,但他运用的历史学语言含苞欲放,似有将政治与文化、疾疫与科技、社会与经济熔于一炉之势。倘若这一视角能够贯彻全著,此书章节之间的张力和潜力便不可同日而语了。
时与史
《旧世界的相遇》是一部1993年出版的旧书,时隔二十二年中译出版,可以说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相遇了”。“但有前书堪读,并无成法可‘宗’”(李渔《闲情偶寄》)——本著也值得“宗敬”,但不宜“宗附”。不论二十年前还是两千年前,引入国外书籍总是顶好的事,但读者必须清楚意识到文本的时代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宗奉”洋经,当作武功秘籍修习,以免经脉错乱。本先生文笔颇佳,但也不无古怪之处,如在族群名称前总是不加定冠词(如原著87、139、170页)。他用词乖张,却更加mortifying:说朱元璋是“威权主义将军”、永乐是“洪武的接班人”,译者明智,不予采用。本先生说郑和下西洋“有极少结果,或者说没有任何永久性结果”,译者改为“没有产生长期的影响”,更贴近事实。本先生称赞郑和不强推“文化与意识形态”,译者去掉了现代批判理论概念,仅保留宽泛的“文化与价值观念”,这也更加符合历史叙述的严谨性。通常是译文不堪卒读,此书的译文却悄然约束了原文的狂放不羁。
长期以来,人文与社科忽视宗教,导致许多阐释机制显而易见却无人问津。之后,学界力图重新找回宗教,或是将信仰当作变量探究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差异,或是在看似世俗的政治理论中找到神学的影子,抑或是打开信仰的黑箱子,像社会学家一样漫步都市、像人类学家一样踏遍村落,试图理解怀抱着种种信仰的普通大众究竟为何如此言行。但本特利先生的“万变不离其‘宗’”确乎不是在有意识地重塑学术视角的宗教性,而是怀着“改宗式相遇”的念头去堆砌史料、释读史料、编织史论,无怪乎谈着谈着“文化”便绕回了“皈依”。这是此书本可以预见的批评、本可以做出的回应、本可以弥补的遗憾。“长时段”“跨疆域”的宗教碰撞是个热辣的课题,很容易在公共领域产生回响,也更容易拿到学术奖金。但取缔传统“世界史”的“国际史”和“全球史”能否健康地跨越时空探索文化交流史,而不拘泥于“宗教碰撞”的拜物主义,而是返璞归真地文化际遇?我想,我们一旦“悬置”先入为主的叙述框架,静静地听古人发声,“君之‘宗’之”,便会发现:他们自己讲的话也是那样富有启迪。
尾声:改宗,抑或不改宗?
本特利先生耳顺而陨,未及古稀,为后威廉·麦克尼尔时代的世界史留下一丝悠悠怅念。夏威夷的阳光滋养了这位抵住史学分流,既不柴米油盐也不语境观念,只是坚持跨疆域、大叙述的世界史家,但波利尼西亚的海浪并没有卷走盎格鲁-萨克逊学者的宗教意识底色。《旧世界的相遇》终究是《旧世界的皈依》,贸易和科技跨越的文化边界,超不出信仰与崇拜的精神边界。本特利提出的文化相遇,实是剔除了历史错置与统计文盲的“文明不必冲突论”,而其中的“文明”正如双子塔塌陷后美利坚公知口中的“文明”一样,成了制度性宗教的别称。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本先生审视的是在法兰克人淫威下皈依基督的萨克逊,是回鹘单于城里的粟特摩尼信徒;是长安的十七景僧讲福音,是蒙古毡房中的回回和喇嘛……这位追溯旧世界如何相遇的旧世界史家不但随十字军东征,也随铁木真西征,甚至随郑和游南洋,但所到之处,他逢人便像哈姆雷特一样喋喋不休:“是皈依,还是不皈依?”大大局限了他的阐释学空间。在这个文明对话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文明对话的效果出奇低下的时代,我们大可以从“互信仰”视角出发奠定“互信”之基础,但更有必要培养宗教论域以外更为普遍的“信”。如何剪掉心中那根“信与不信”的辫子,也改一改“宗”,是所有“走向全球”的世界史家“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都大可以“增加勇气”,自我诘问的。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非本网原创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